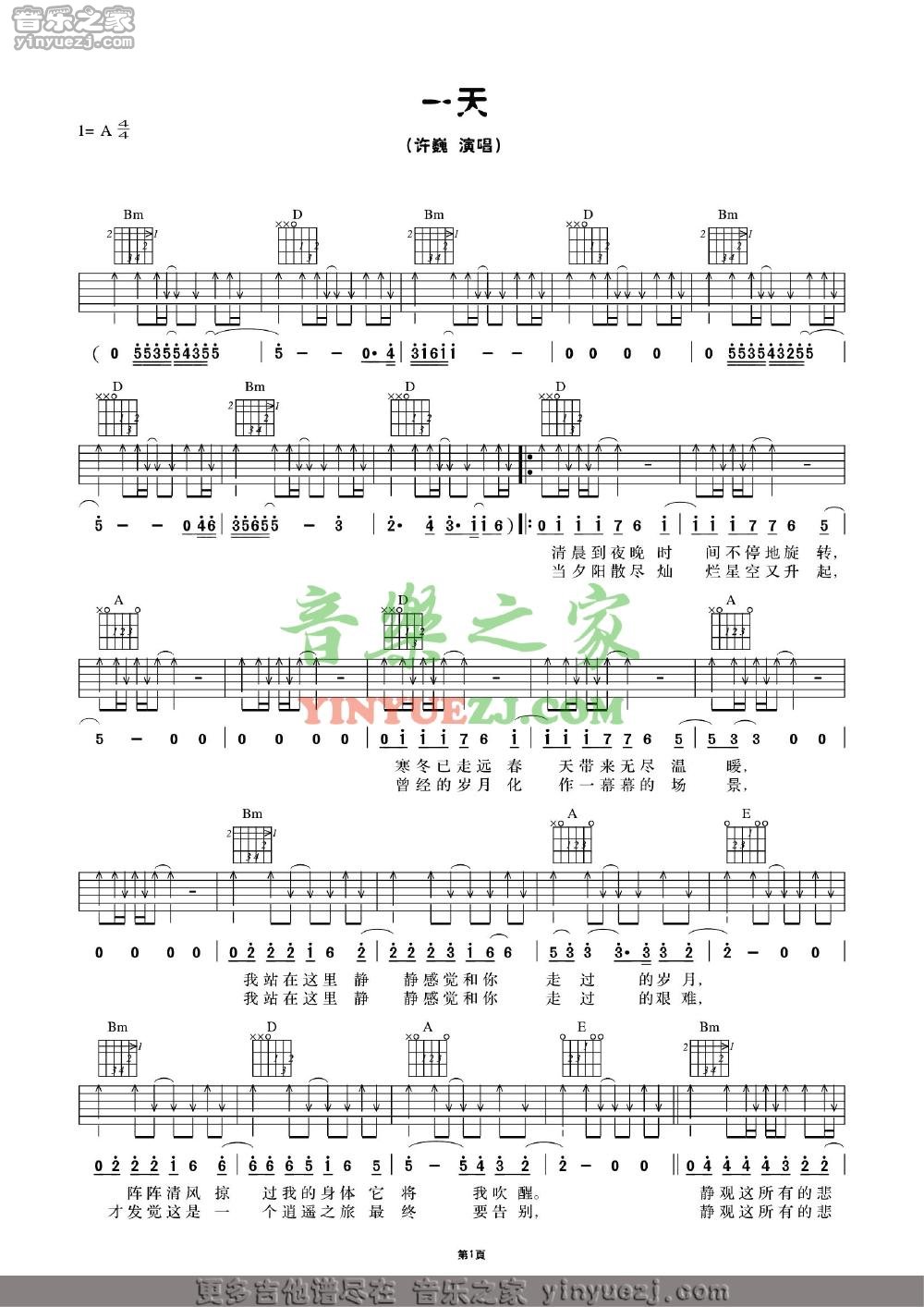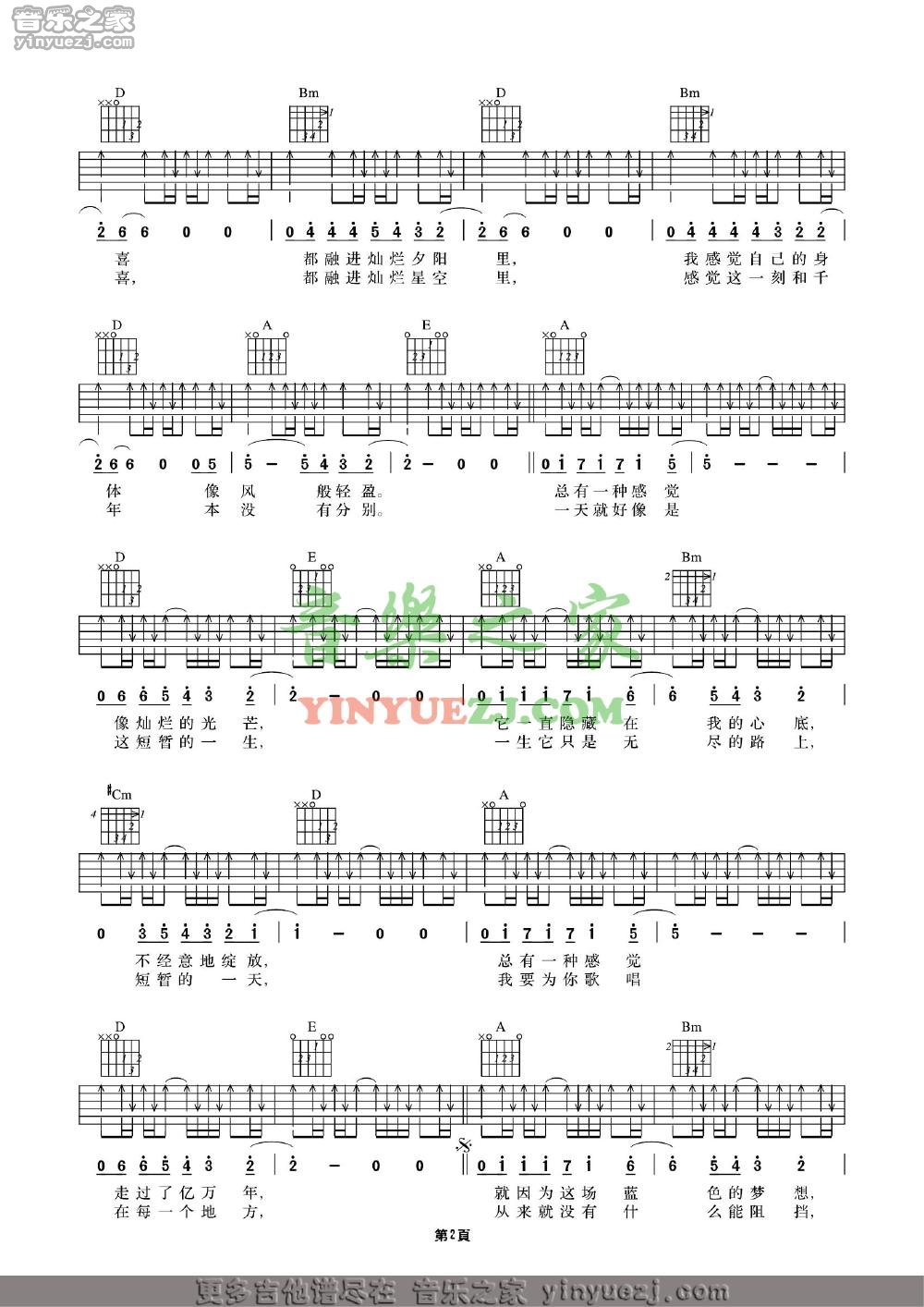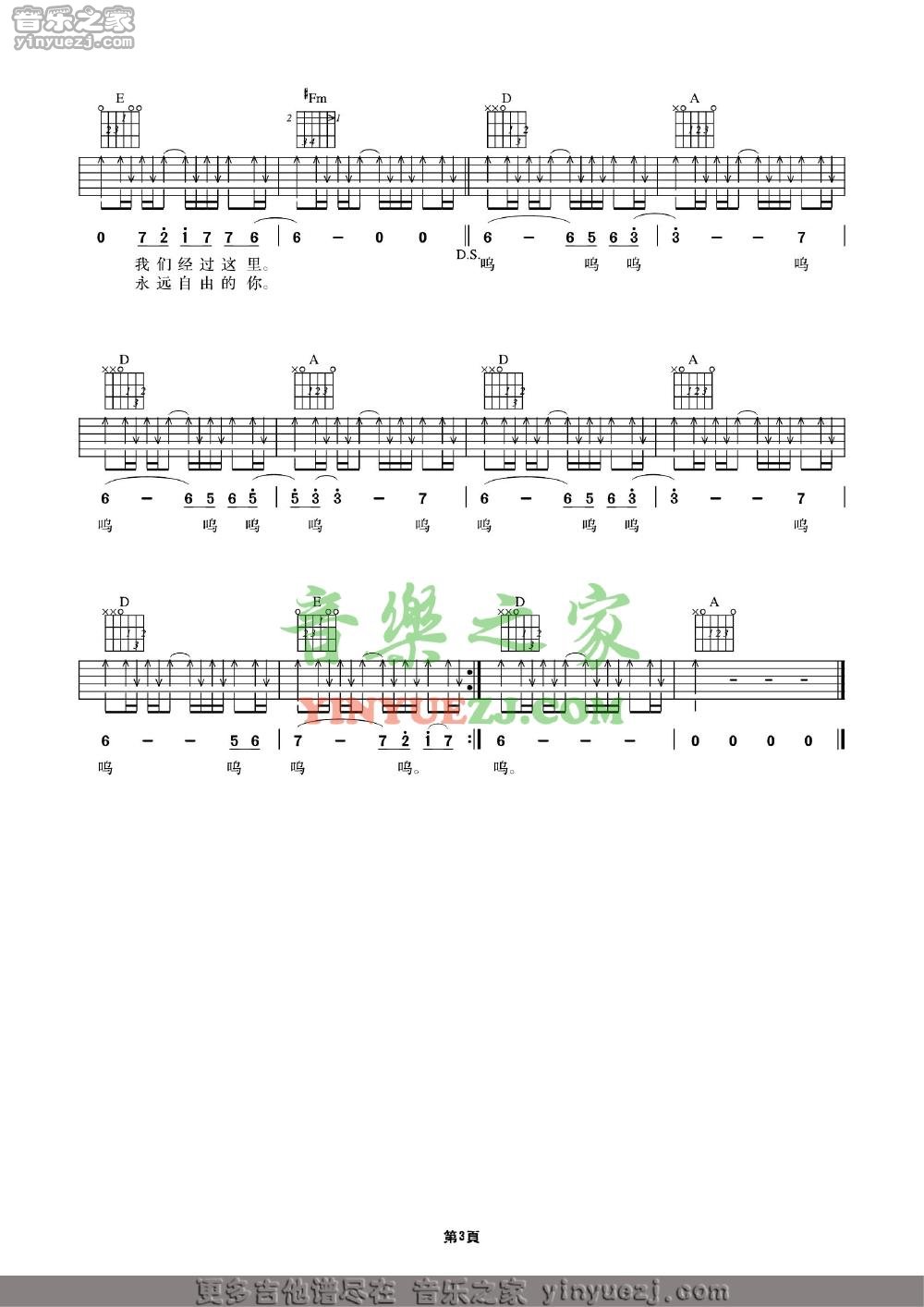《一天》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都市人共有的时间焦虑与存在困境,将二十四小时压缩成生命状态的隐喻符号。晨光中的闹钟不仅是物理时间的刻度,更象征着现代文明对自然生命的规训,咖啡杯里荡漾的不只是提神饮料,而是个体对抗机械性重复的脆弱武器。地铁玻璃映出的模糊面容揭示了数字化时代的人际疏离,人们在移动网络中保持连接却失去真实触碰的能力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未读消息"与"待办清单"构成双重枷锁,量化生存的背面是精神家园的持续荒芜。傍晚的晚霞被处理成手机滤镜效果,暗示自然体验已退化为可编辑的虚拟符号。深夜独处时刻的自我审问暴露出存在主义危机——当所有时间都被社会时钟切割标价,那些未被消费的空白反而成为确认自我存在的最后疆域。全篇通过蒙太奇式的生活碎片,展现后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过程,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述里埋藏着对时间暴政的沉默反抗。电子日历的红色标记不断吞噬生命的原真性,而人们仍在算法的指挥下跳着永不停歇的圆舞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