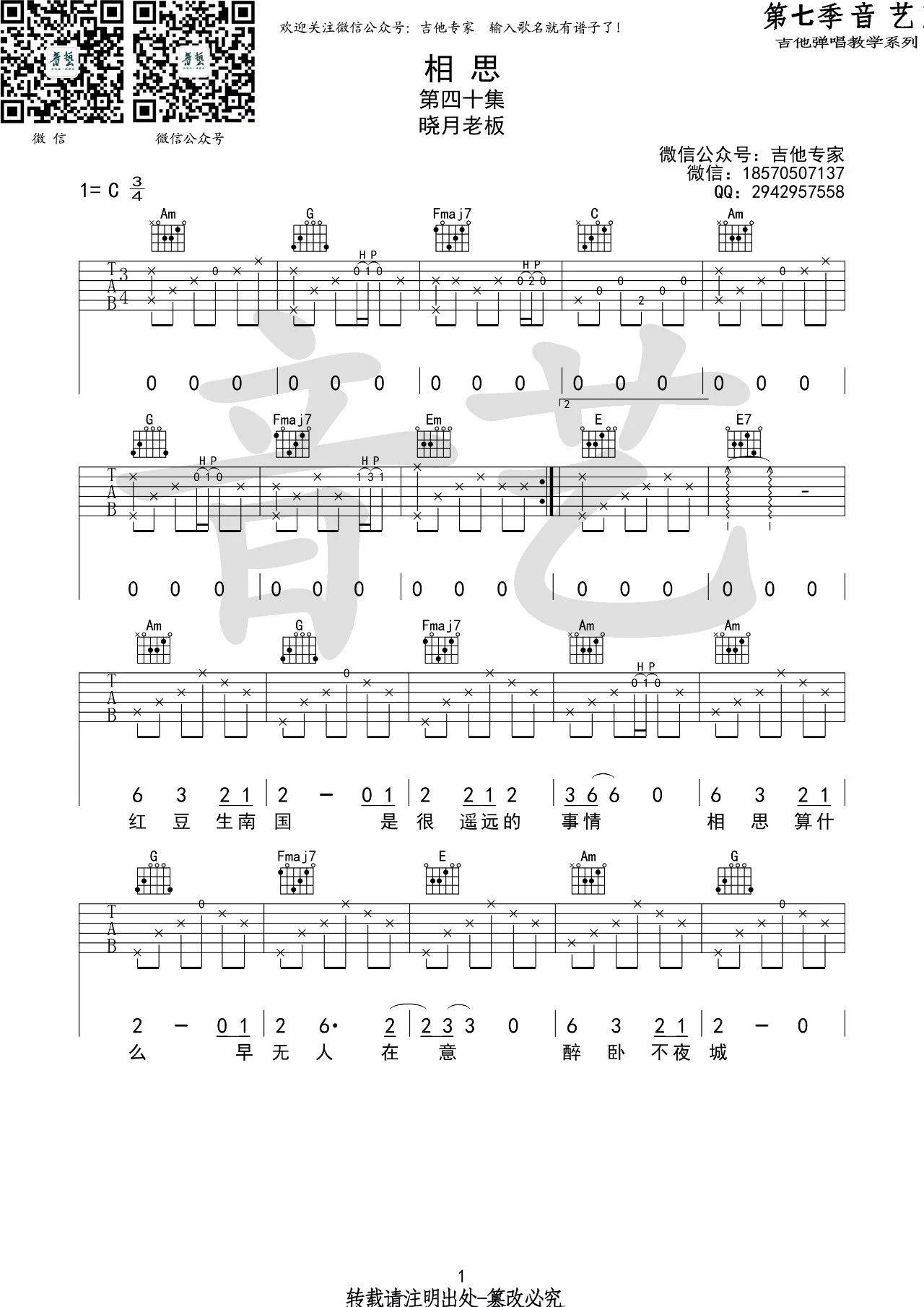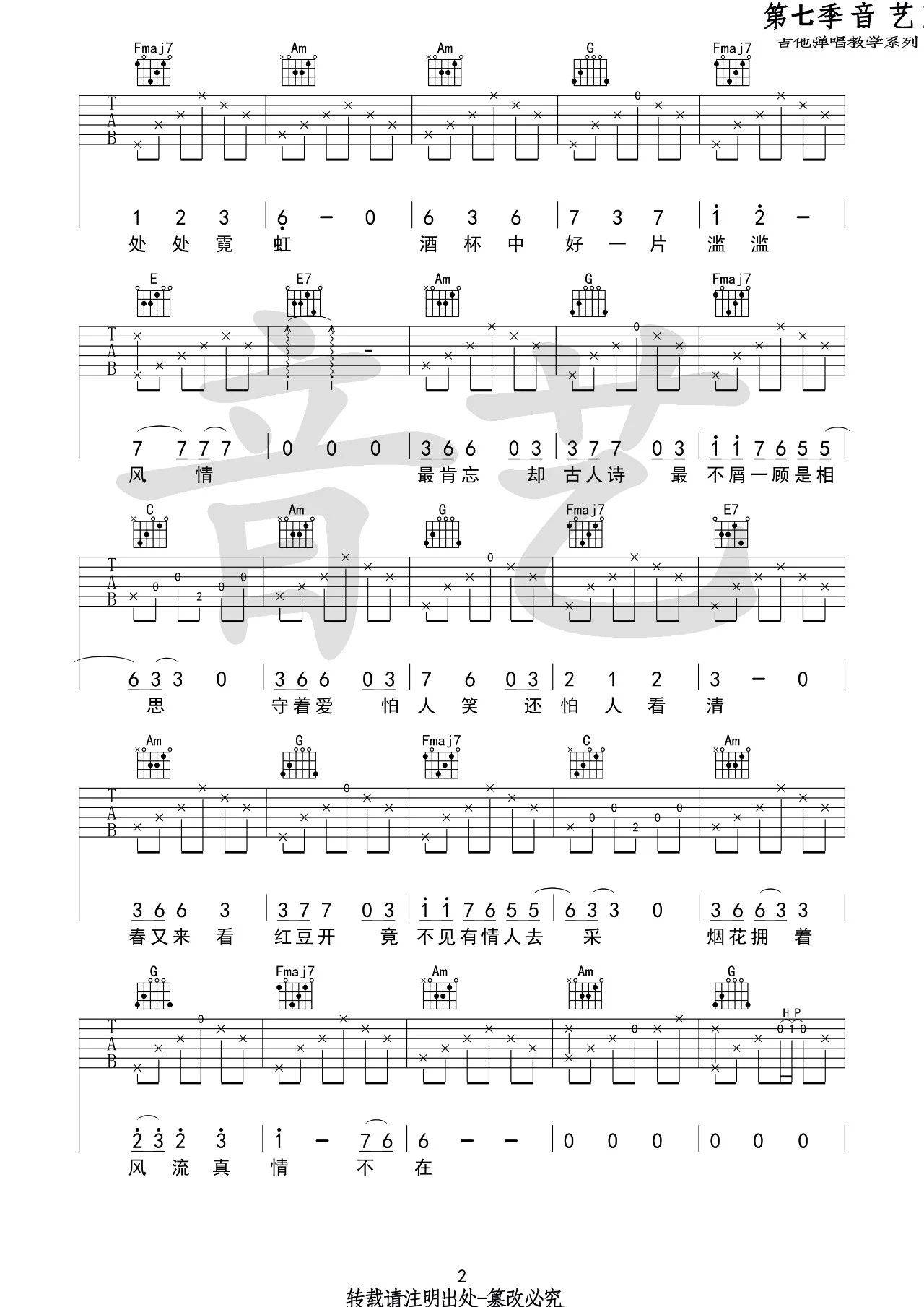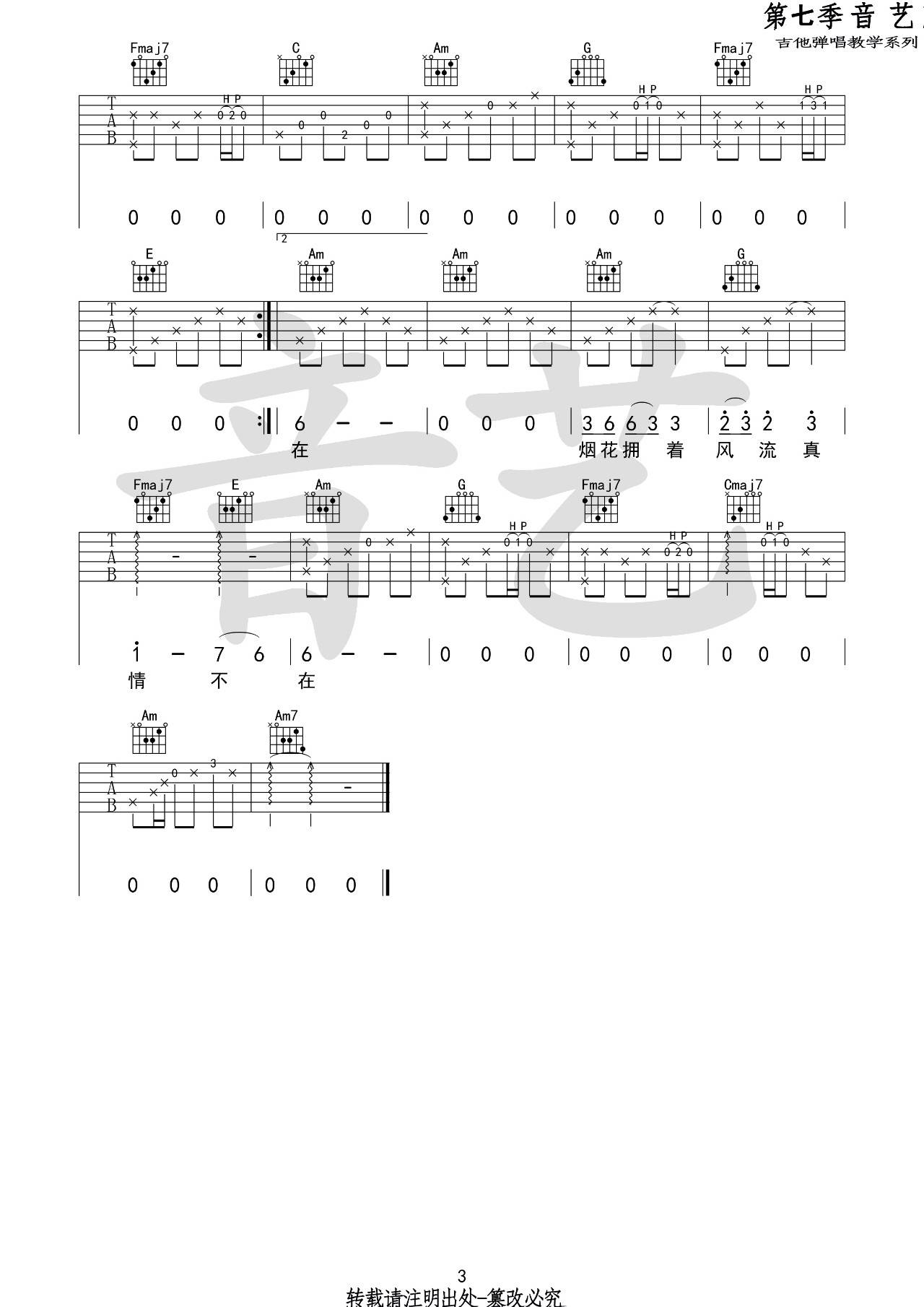《相思》以含蓄婉约的笔触勾勒出东方美学特有的情感意境,通过红豆、南国、春风等古典意象的层叠铺陈,构建出一个缠绵悱恻的抒情空间。歌词中"红豆生南国"的起兴既是对王维诗意的化用,也是对千年相思文化的隔空呼应,将植物萌芽的自然现象升华为情感萌动的隐喻。文本中反复出现的"等待"与"采撷"形成时空交错的蒙太奇,未完成的动作暗示着永恒的期待,而"最相思"的叠句则如心跳节拍般强化着情感的律动。风雨、年华等意象的介入为抒情注入沧桑质感,使相思之苦超越儿女情长而触及生命本质的孤独。全篇以物喻情的表达方式延续了《诗经》"托物起兴"的传统,红豆的鲜艳色泽与柔软质地恰似情感的炽烈与脆弱,而"此物最相思"的收束则将具体物象彻底抽象为情感符号,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审美飞跃。这种将文化记忆、自然意象与生命体验熔铸一体的创作手法,既是对古典诗词意境的现代转译,也揭示了人类情感跨越时空的永恒共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