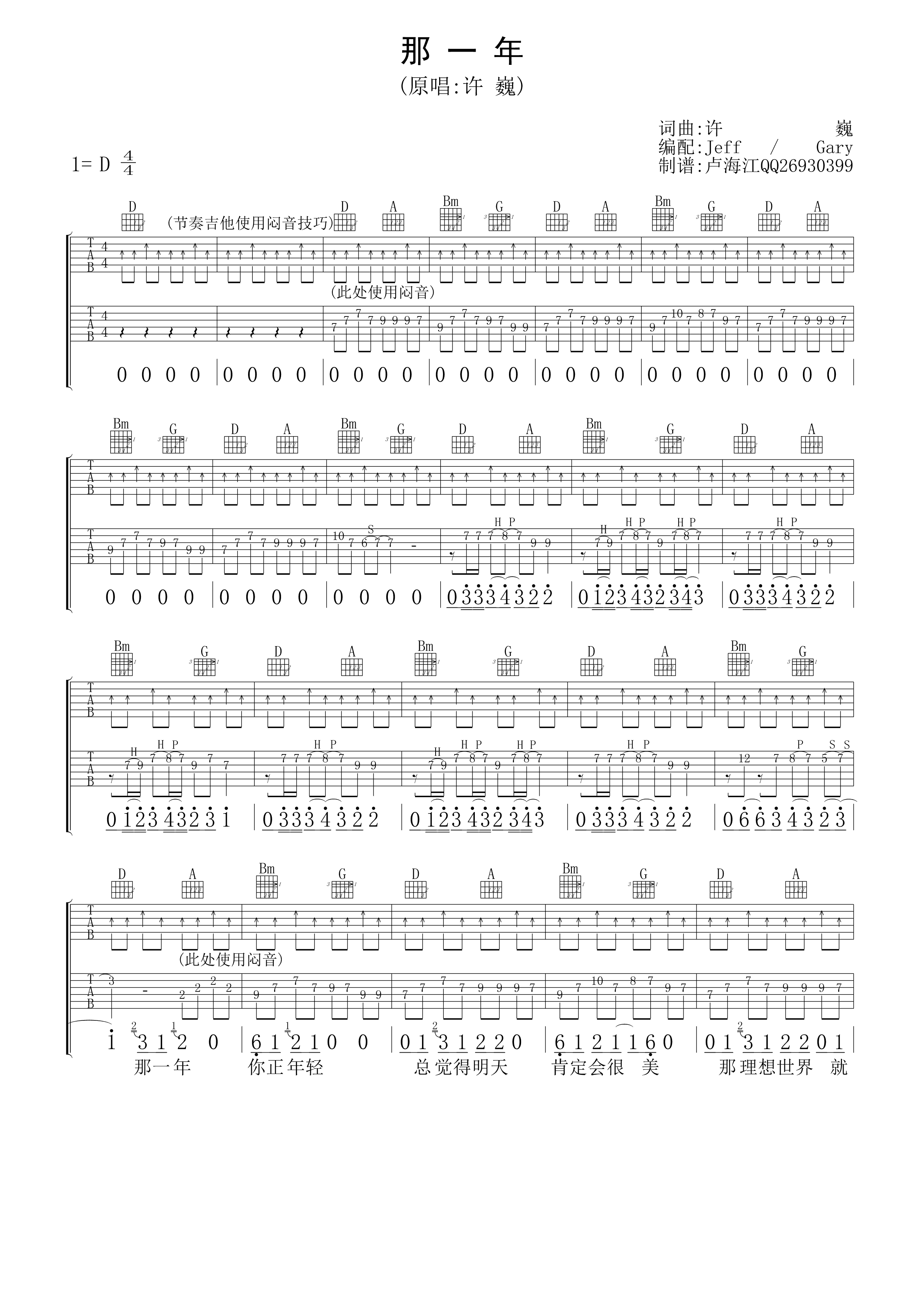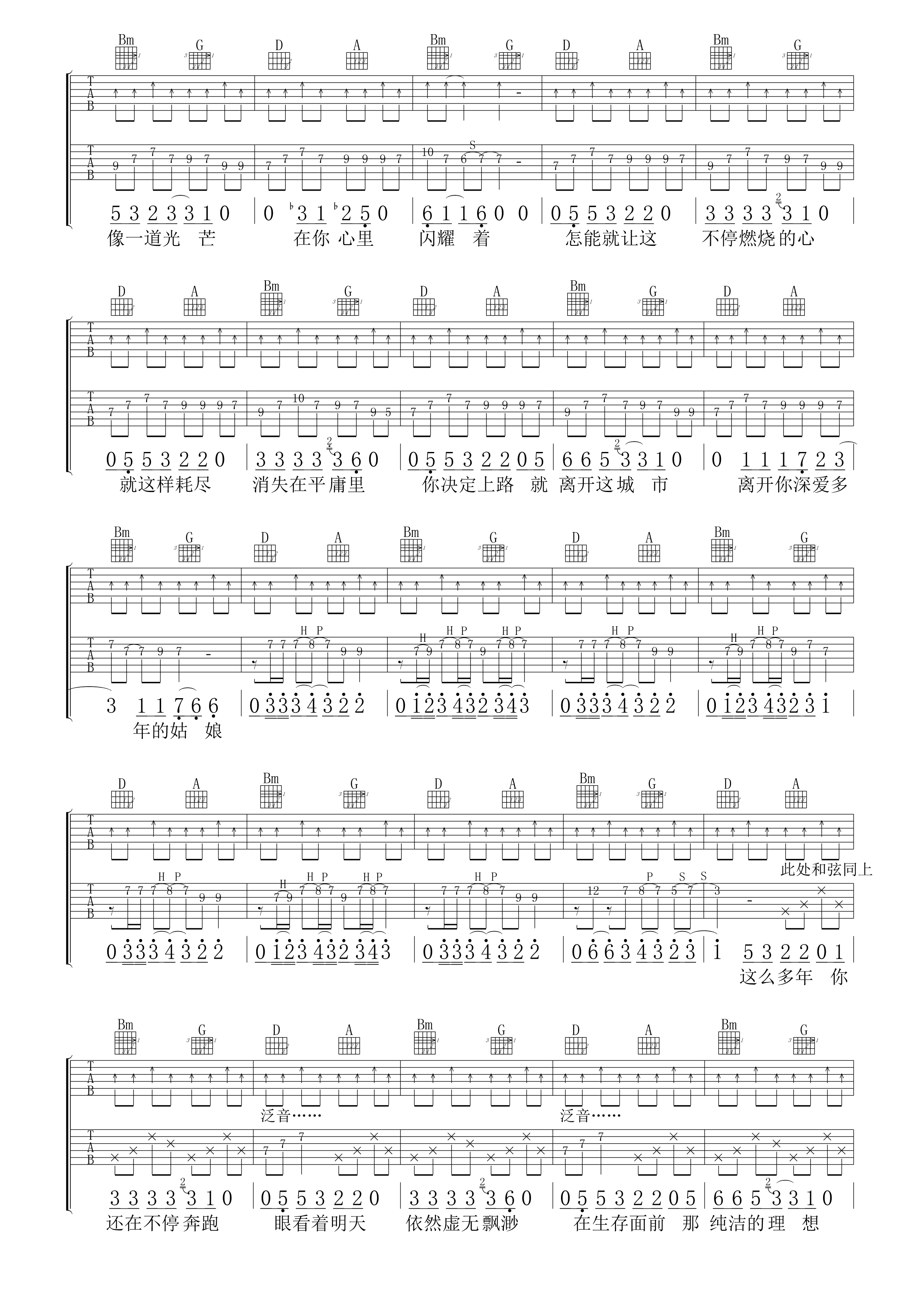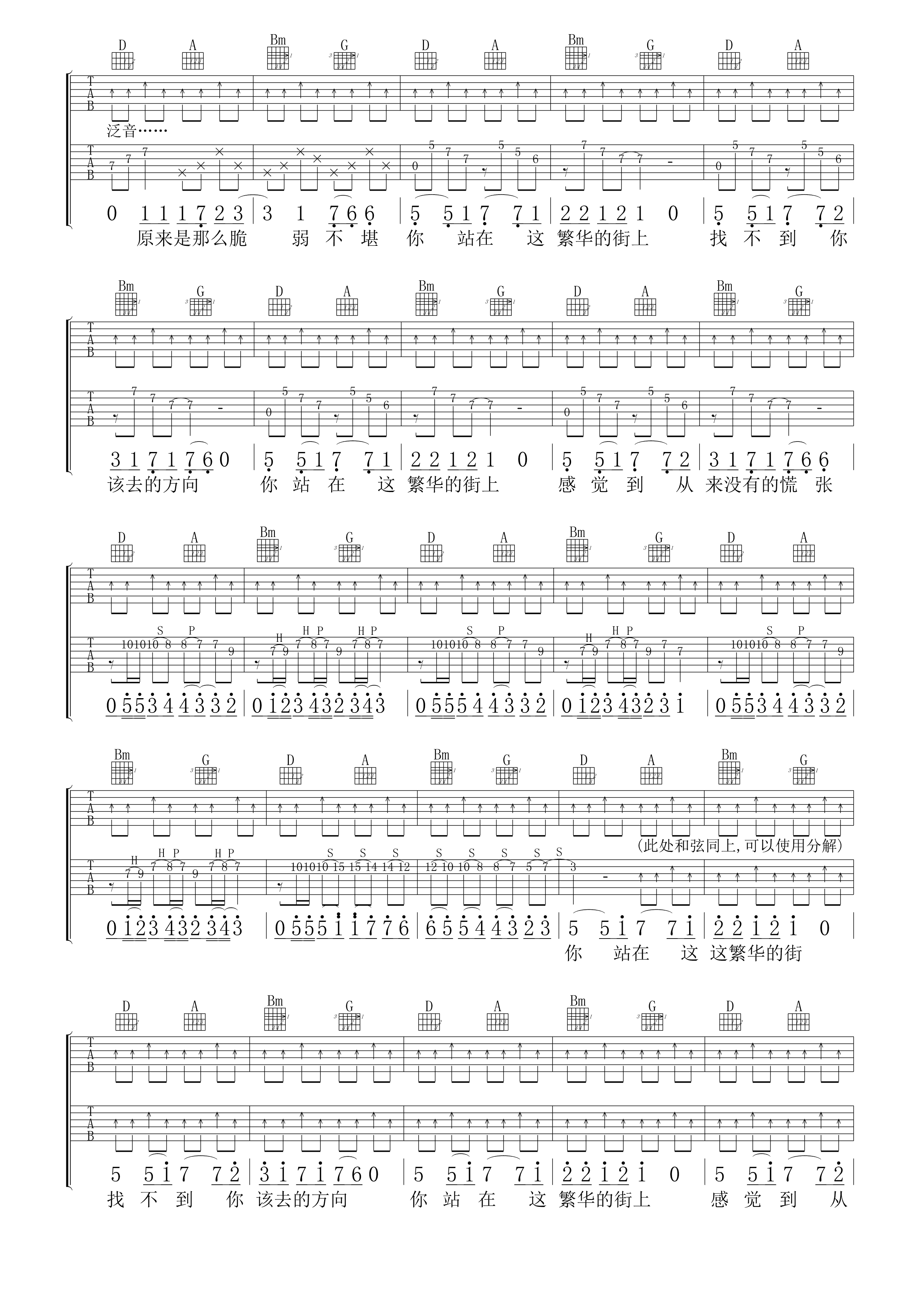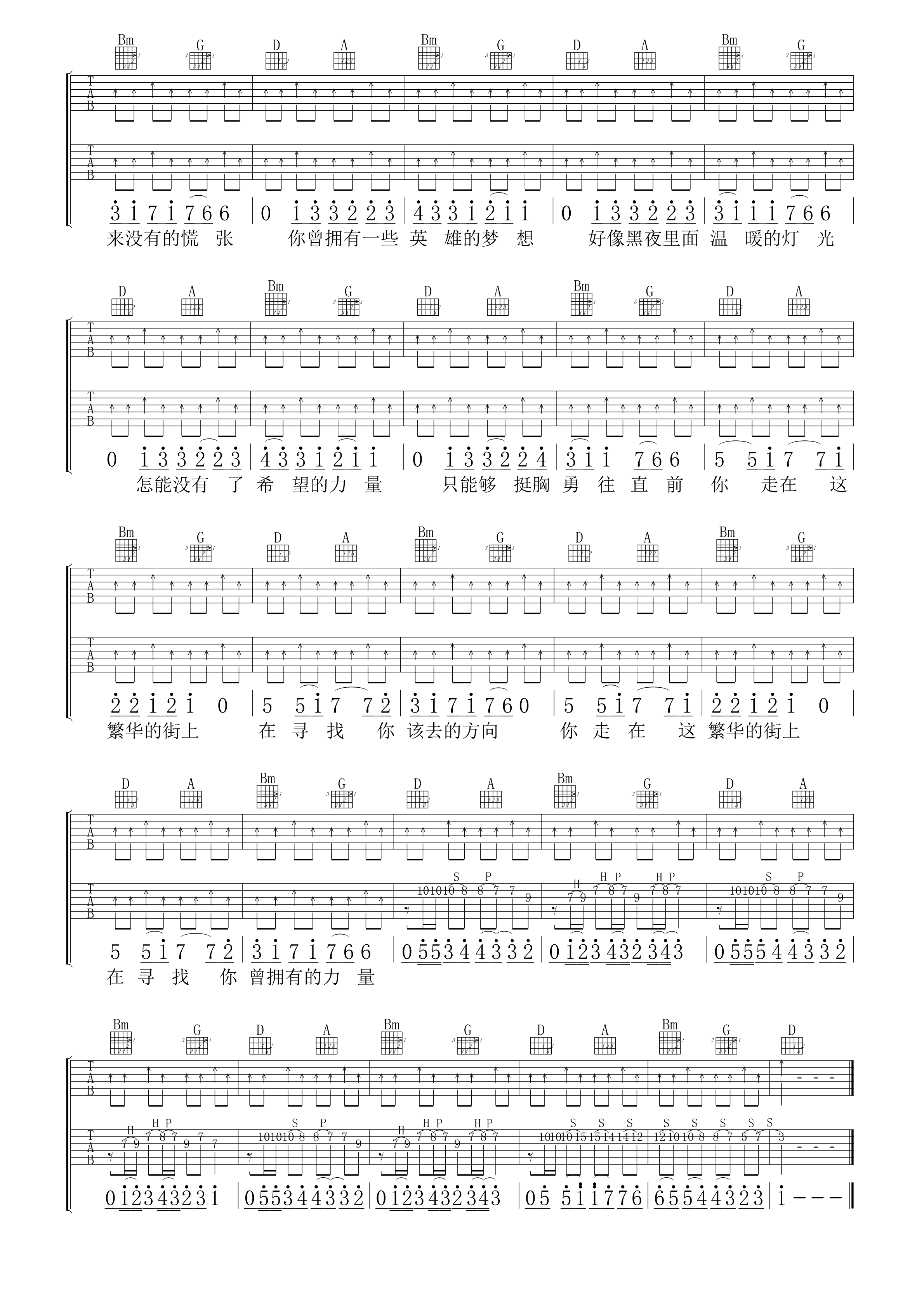《那一年》以蒙太奇式的意象拼贴,勾勒出青春记忆的斑驳质感。锈迹斑驳的单车铃声与褪色校服褶皱共同构成时空锚点,将听众拽入泛黄的时间流域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“未拆封的信笺”与“午夜电影院褪色的票根”,实则是情感悬置的隐喻—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告白与未竟的约定,在记忆的真空封装里发酵成永恒的可能。蝉鸣与紫藤花的嗅觉记忆形成通感式书写,证明身体比理智更忠实地保存着时光的拓片。 副歌部分用“逆光的站台”与“永不靠站的绿皮火车”的悖论意象,揭示青春本质的荒诞性:那些看似无限延展的可能性,实则早已在时空坐标系中凝固成注定错位的轨迹。雨水中晕开的蓝色墨水作为核心意象尤为精妙,既指向具象的书写痕迹消逝,又隐喻记忆在反复回味中产生的形变。最终停留在老墙斑驳处的光影移动,实则是将宏大的岁月流逝具象为微观尺度的侵蚀痕迹,这种举重若轻的处理方式,使时间呈现出既温柔又残酷的双重质地。 整首作品通过物象的考古学发掘,构建出关于遗憾的美学体系。所有具象物品都成为情感化石,在记忆的地层中保持著精确的时空坐标,而正是这种精确性,反而凸显了人与旧时光之间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。